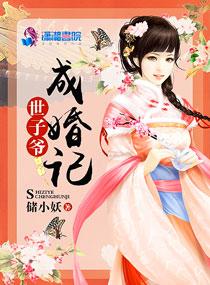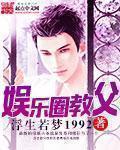630中文网>河东与河西的故事简短 > 第191章 焦土深根藏春讯 墨淡荒斋立铁肩(第1页)
第191章 焦土深根藏春讯 墨淡荒斋立铁肩(第1页)
1971年的夏末,河西岸的风裹挟着麦秸秆焦糊的气息,沉重地拂过小姬庄低矮的土坯房檐。
村头那棵虬枝盘结的老槐树,叶子黄了大半,打着旋儿飘落下来,在晒谷场上铺了厚厚一层,又被社员们脚上沾满泥浆的布鞋反复碾踏,最终化作齑粉,融进这片贫瘠的土地里。
空气里还浮动着特殊运动留下的硝烟味,刺鼻而干燥,但若深深吸一口气,又能嗅到一丝微弱的、异样的生机——
公社斑驳的公告栏上,“抓革命促生产”的红漆大字依旧触目惊心,可就在那朱红的下方,一张张写满工分与粮食斤两的秋收预分表,如同新生的苔藓,悄然贴了出来。
学校那被风雨剥蚀的土墙,“以学为主”的新标语,正努力覆盖着去年“砸烂旧教育”口号残留的狰狞墨迹。
姬永海背着洗得发白、边缘已经绽出线头的帆布书包,沉默地穿过晒谷场。
记工员老田正蹲在冰冷的石碾子上,嘴里念念有词,铅笔头在一张被油污和汗渍浸润得发黑的纸上艰难地滑动:
“姬忠年他爹,昨儿割稻子,十分工;
庞四十娘,喂猪八分工……”
姬永海放慢了脚步。
这记分册上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数字,竟像一根根倔强钉进河滩淤泥里的木桩,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、让人心头微颤的“稳当”。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书包里那几本磨得卷了毛边的课本。
封面上“小学五年级”的字样几乎被手指摩挲得难以辨认。
这书,比起前两年上课时老师手里挥舞的、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,已经是天大的稀罕物,是照亮河西贫瘠精神荒原的一缕微光。
学校的土教室是真正的“土”教室。
黄泥糊的墙壁坑坑洼洼,屋顶的茅草年久失修,每逢雨季,教室里便叮叮咚咚,奏起漏水的交响。
但这学期,那面烟熏火燎的土墙上,竟破天荒地钉上了一张课程表:
上午语文、数学,下午农业基础、革命歌曲。
只是课桌依旧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土坯台子,学生们自带的高矮不齐、吱呀作响的板凳,更是让这教室像个杂货铺子。
上课铃那破锣般的嗓子一响,底下便常有按捺不住的学生扯着喉咙起哄:
“老师!开卷考试嘛,不如放我们回家自己琢磨!”
更有胆大妄为的,真敢一把抓起讲台上的粉笔盒,往地上狠狠一摔,梗着脖子喊“师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,关系平等”,硬是把老师堵在教室门外。
每当此时,教室里便瞬间开了锅。
三五成群的孩子聚成一堆。
有人拿着课本念得字错音,不成句;
有人一把抢过别人的作业本胡乱涂抹;
铅笔头在纸上划拉出歪歪扭扭、不知所云的线条,倒也喧嚣出一种病态的热闹。
姬永海是班长。这顶小小的“乌纱帽”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他总是在这片混乱达到高潮时,像棵被狂风吹弯又倔强弹起的芦苇,慢慢地站起来。
他的声音不高,甚至有些干涩,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韧劲:
“都别闹了!老师教的总比自家瞎琢磨强!”
底下立刻有嗤笑声响起:
“死脑筋!”
但他只是梗着脖子,清瘦的脸颊绷得紧紧的,目光像钉子一样扫过那几个最闹腾的角落。
那无声的压力竟比喊叫更有力,喧嚣竟也一点点地平息下去。
他知道,这年月读书,如同在河西这片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秧,徒劳得近乎荒唐。
可秧苗再羸弱,总得有人弯下腰,用冻得通红的手,一株一株,颤巍巍地扶起来。
教室的四个角落,仿佛被无形的时光之手,钉上了四个截然不同的刻度。
姬永海坐在最前排,脊梁挺得笔直,课本的空白处密密麻麻爬满了他的批注,字迹清瘦有力,如同他这个人。
隔着三排,田慧法正埋头于课本的封面,铅笔尖飞快地游走,勾勒出一条活灵活现的鱼——
正是昨天在村后那条浑浊小河沟里摸到的那条,尾巴翘得老高,仿佛要挣脱纸面,跃入想象的清流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芒种 入陷(1v1) 把小秘书吃干抹净的日常 忍界强者,但一直被嬷 火影:踏上最强之路! 综武:开局成为燕十三! 玖辛奈为了变强勾引鸣人直至怀孕 天衍城:星轨织忆录 主播他其实很乖 亮剑:旅长,求求你别打劫了! 小富即安的平淡生活 凤倾天下从蛇灵逆党到女帝 嘘,穿进这种书就要没羞没躁! 游戏失败后沦为boss们的性奴 锦衣听香风满楼 资治通鉴新译 三国群美传 萝太弟弟如妹妹 少妇吕媚 掳母之乳海情深